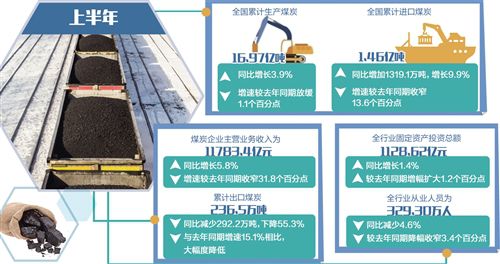全球今热点:人间有味 | 寻常 :食野
2023-06-28 21:12:09
来源: 顶端新闻
鸡啼朝暑,蝉鸣晚树,这浮生、思量成句。荏苒流年,且教我、慵人偷误。又闲过、几番晦雨。
东厅执箸,西厢寐寤,应东坡,嘲人俳语。措大豪言,却到我、解聊寻趣。这般人、咎由自取。
——《解佩令·自嘲》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《东坡志林》里记载着这样一则笑话:“有二措大相与言志。一云:‘我平生不足,维饭与睡耳。他日得志,当吃饱饭了便睡,睡了又吃饭。’一云:‘我则异于是。当吃了又吃,何暇复睡耶?’”措大,又称“醋大”,指穷酸书生,如中举前的范进,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。忘了之前在哪本书里看过,里面把它翻译成“乞丐”,我觉得更贴切一些。
这两位“措大”的“高谈阔论”,细细品味,也有些道理在里面的。人之于世,做得最多的不就是吃喝拉撒嘛,人的一生,把这些都对付好了,可是很不容易的事。若从每件小事里都能寻到一些趣味,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人。
我平生也是吃过一些好吃的的。
我亦想学着做一个有趣且热爱生活的人。
菌菇
不知从何时起,人们开始不大认得野生的菌菇了。尽管它们长相很可爱,闻起来也鲜美,但你不好分辨,是有毒还是无毒?所以不敢乱吃。也因此错过了很多美味,实在可惜。菌菇炖汤,极鲜美。不管是什么菇,我就没见过有菌菇炖汤不好喝的!
菌菇的种类很多。在乡下,夏夜下了一场雨,第二天,路边,山上,地里……全是各种各样的菌菇。栗树菇、枞树菇、茶树菇、雷打菇、胭脂菇……我一时想不起许多名字了。
栗树菇多生在栗树下,故名。岳西多板栗,我老家东面有条小土路,路边有地,地里就种了很多栗树。夏夜一场雨后,路边全是这种菇子,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。有的长得太快,水分跟不上,伞沿处已经开裂。就一夜功夫,这玩意长得是真快!栗树菇的菌盖为灰白色,白色居多,只有近中心处是灰的。味道,味道……完了,好多年没吃过,我竟忘了栗树菇什么味了!
枞树菇又称松乳菇,多长在林间,地里少有。凡有松树生长的地方,几乎都有它的影子。岳西山上多枞树(即黑松),故也多枞树菇。菌盖幼时半圆形,中间下凹,成熟时平展,无嗅无味,肉质鲜嫩。小时候采到一根枞树菇有脸盆大,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菌菇了。
茶树菇,因野生于茶树的枯干上而得名。菌柄细长,中实,菌盖较小,红褐色,多丛生。用晒干的茶树菇佐汤,极鲜美。
雷打菇是方言,书上查不到,我是从二妈那里听来的。雷打菇多在大雨打雷过后的竹林和烂草丛中出现。不仅如此,它长得也黑黢黢的,黑得还不均匀,带点灰,又带点黄,蓬头垢面,真像被雷打过一样。个子也不高,扁头扁脑的矮矮一坨,说实话,真丑。虽不中看,但味道香滑可口,是菌中美味。
胭脂菇是我见过最好看的菌菇了,菌盖小巧,色如胭脂,微白,是个美人胚子。长辈说这种菇子吃不得,有毒。果然越好看的越有毒。还有一种说法,说胭脂菇就是红菇,红菇是可以食用的。我分不清。
岳西山里有一种菌菇,状如白伞,菌盖呈丝网状,菌柄修长,有细细纹理,视之如白蛇蜕皮,二妈说这叫蛇皮菇。小时见过一次,这玩意能吃吗?二妈采回家炖汤,肉质鲜美无方,至今思之咋舌。可惜山中很少见,此后未曾尝过。用一句老话:“一日食此菇,三月不思肉”来形容,一点不过分。
听说鸡枞是菌中之王,可至今未尝其味,可惜。
笋
春节后下过几场雨,春笋就都冒出来了。像一只只孩童,探出尖尖的脑袋,它们小心地窥探着地外面的世界。不几天,你再去看它,这时你们身份对换,它们看你像小屁孩了。雨后的春笋,长得不是一般的快。
山中多野果,多野菜,多山菌,但人们最喜欢的,当属竹笋。我的家乡菖蒲镇,山上多修竹,有“茶乡竹海”之称。每至清明前后,下了几场细雨,参差错落,满坑满谷,全是竹笋。春笋人们多不舍得吃,是要长成竹子的。竹子长大后能卖钱,对于种地的庄稼人来说,是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但山中还有一种细笋,只人手指粗细,皮色青绿,笋肉白里透黄,带露水清香,味道清美,相比于春笋,有过之而无不及,然乡人多不吃,不知为何。在外涮火锅,一碟细笋,卖十几块钱。这玩意在乡下,一采一大把。小时候我跟二哥在山上折了好大一捆,回家剔去笋皮,切宽丝,放开水里焯两焯,拧干置笸篮晒干,制成笋干。笋干久贮不坏,什么时候想吃了,擎几片放火锅里煮,别有风味。
至年底,就有很多人掮着锄头去竹林里挖冬笋了,冬笋长不成竹子。他们挖冬笋有的是自己吃,有的拿去卖,能卖十块左右一斤。听闻乡里有擅挖冬笋者,一天能挣五六百。我也挖过,挖了一天,汗流浃背,挖冬笋还真是个力气活!啥?问我挖了多少钱?二三十。我挖冬笋纯是觉得好玩,不为吃,也不为卖钱。
乡人都称冬笋是美味,我独对其不怎么欣赏。吾友敏轩改苏轼《猪肉颂》以戏之:“岳西好冬笋,价贵如黄金。寻常不解煮,却说不好吃!”
我确实不解煮,这边冬笋卖得也是真贵。
薇菜
“采薇采薇,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,岁亦莫止。”小时候就读过这首小诗,很懵懂,也有很多不明白。“薇”是什么呢?不知道,就过去了。稍大了一点,见《史记》中又载着伯夷与叔齐“不食周栗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”,后人又以“采薇”比喻“归隐”,薇长在深山里,噢!那么“薇”就是薇菜了!——好长时间我都这么以为。但凡当时仔细看一下《诗经》的注解我也不会把“采薇”当成“采薇菜”了。《说文》:“薇似藿,乃菜之微者也”,大概是类似于野豌豆类的植物。
为什么我听说伯夷与叔齐在首阳山里采薇而食就以为是薇菜?野生的薇菜就长在深山老林里,很多,又可以吃,所以让我产生了一种误解。小时候我就经常去山里面打薇菜(我们那边发言称“采”为“打”)。薇菜根茎粗壮,顶部叶子卷屈着,卷成一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小脑袋,外侧生有白色绒毛,长相可爱。长大后叶子逐渐展开,作羽状分裂。薇菜长大后就不能吃了,纤维太粗太硬,咬不动。
薇菜生长的季节我不乐意。它四月抽芽,五月成熟,那会儿我正在学堂,坐在咯叽作响的旧木椅板凳上,对着枯燥的课本和讲台上老师无聊且凶巴巴的脸。只有捱到双休,我才有机会去山里打薇菜。
打薇菜是很好玩的。背个麻袋,带把弯刀就上山了,山里多灌木,带弯刀是用来开路的。那种在灌木丛里穿梭的新奇体验,斑蝥拂过手臂与脚腕的快感,发现正楚楚而立着的薇菜时的激动心情,日翻高山越长岭十数里,亦感觉不到丝毫疲惫。打薇菜须眼力好,眼观四路,不放过每一处它可能会生长的地方。有时它们躲得很深,与别的野草长在一起,你需能够分辨,这都是考验眼力的。山中有一种草,跟薇菜长得很像,一样卷着圆圆的脑袋,一样披着绒毛,连打开叶子都一样,一看简直是薇菜的孪生兄弟。不同处是它的绒毛长长的,灰黄色。小时分不清,看到也一起打了回去。晚间,一家人在白织灯下,中间撑一个大笸篮,围坐着剔薇菜(采回来的薇菜须把卷屈的叶子与绒毛用手指小心扯去,只留下中间的茎,才能吃)。奶奶看到那个草,举手上问:“哎也!这是哪个打回来滴?想闹死(即毒死)我们呦?这是断肠草,吃不得,能闹死人滴!神农尝百草,就是尝了断肠草被闹死了。”断肠草是我家乡那边的叫法,不是学名上的断肠草,或许是有人不识,张冠李戴,然后竟偶然在某地流传开来。但有毒是真的。
薇菜剔好之后,用清水洗净沥干,抵在五月的太阳底下暴晒,晒干之后储藏起来,可作家常小菜,也可佐火锅,味道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,带着一股只有薇菜才有的气味,总之是很好吃的。
毛栗
我的老家岳西菖蒲,家家都种毛栗。毛栗的吃法很多:放锅里蒸,吃起来粉粉的,很香,比山芋还香!放火边烤,更香,但口感比蒸出来的稍差;剥去皮,放缶里煨,加猪肉与适量白糖,香甜可口;放锅里添糖爆炒,糖炒栗子,甜里带香;生吃,香中带甜,生吃一次不能吃多,吃多了易放屁,吃过毛栗后放出的屁尤臭!吃毛栗除了放屁是臭的,其他全是香的。
毛栗蓬结在树上,旧时要吃的时候就用晒衣服的篙子敲下来。敲的时候可得小心,毛栗蓬上都是尖尖密密坚坚的刺,落在人头上那滋味可不好受。别问我怎么知道,小时候头都被砸烂了!农村里有小孩子不听话,大人就说:“你再胡闹!再胡闹就给你一个大爆栗子!”什么是爆栗子(也有作栗暴的)?将食指、中指弯曲起来砸人头顶,像毛栗蓬砸在人头上一样。
地心菜
地心菜即荠菜,是我们这边的方言。地心菜是野菜,人家不种,但路边,地里,墙角边,都有生长。准确说它应该是一种野草,一种可以吃的野草。
有时候人们吃腻了萝卜白菜莴笋,觉得不够过瘾,偶尔会想起它。想起它时,提个箩到路边地里找,不过一下午,就能采满一箩。
地心菜叶如锯齿,呈莲座状伸展开来,莲座中心生白色花序,花序直立。采地心菜不能等开花,开花了就老了,吃不动。我曾好奇它的味道,长这么大也没吃过野菜,便采了一些回家洗净沥干,晚饭时夹一些放火锅里煮,味道还可以,但太“粗”了,吃在嘴里硬硬的,还有细细绒毛,口感不佳。
地心菜晒干还是一味药材,和脾,利水,止血,明目。
毛香粑
岳西的特产有很多,毛香粑算一个。
旧时每至清明前后,松林中就生出许多毛香火绒草,也忽多出许多背着箩筐采毛香火绒草的姑娘。毛香火绒草颜色翠绿,茎直立,高不过一尺,多丛生,叶子小巧可爱,毛茸茸的,有淡淡清香,当地人又叫“毛香”。毛香很好看,采毛香的姑娘也很好看。
毛香可做粑,清明前后吃毛香粑似乎成了一种习俗。春季是流行病的高发季节,而毛香茎叶可以入药,有镇咳、祛痰、止喘等功效。把毛香做成粑,不仅有毛香的香味,还有浓浓肉香,清芬可口,又能预防流感时疫,作为美食,深得人们喜爱。喜爱到什么程度?清明上坟也不忘带几个毛香粑供奉祖宗!
毛香粑的做法很简单。将采来的毛香洗干净,用布包起来,拿锤子锤烂后取出,再用排刀切细与面粉和拌。以青葱细肉作馅,搦成粑的形状,放蒸笼里蒸熟,即可食用。岳西县邻县潜山县(现在作潜山市)风土人情皆与岳西相似,也有毛香粑。苏轼是有名的吃货,与潜山颇有些渊源。潜山古时称“舒州”,苏轼老年从琼州北归,被任舒州团练副使,虽只为虚官,并未到任。但苏轼一直有卜居舒州的想法。他写诗说:“年来四十发苍苍,始欲求方救憔悴。他年若访潜山居,慎无逃人改名字”,又写信给舒州的朋友:“偶得生还,平生爱龙舒风土,欲卜居为终老之计”,可惜因各种现实因素,一直未能实现。或说苏轼应是到过舒州的,安庆地方志载有宋代张商英的《游潜山叙寄苏子平》:“少年相老别相逢,月满潜山照肺胸。恩录破除仙录在,世缘消灭道缘浓”,可知苏轼与张商英是一起游过天柱山的。
不觉有些扯远了,我只是想知道,苏轼这吃货,到潜山到底有没有吃过毛香粑?
俗话说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,旧时乡下,有各种山菌、野菜、野果,不烦人种,便可随意采摘。这些遗落在乡间地里的美食,是造物主留给人们的宝藏。但如今很多年轻人对于野菜山菌,都不识得了,不知竟能吃,更不必说烹饪之法。他们更愿意吃超市里买的萝卜青菜,鸡鸭鱼肉。恐怕再过十数年或者数十年,深山里的薇菜、毛香,路边的菌菇、地心菜便无人问津了(似乎现在就已经是了)。
我自小生活在乡下,对于那些野菜野果有着深刻的记忆,确乎有情感在里面的。想到后来人们渐渐不识,它们慢慢地被遗忘在杳无人迹的深山深谷,自生自落,不知其也曾作为美食陈列在人们的饭桌上,心里便作些许遗憾。鸡鸭鱼肉固然美味,但有时若吃腻了鱼与肉,也不妨提锄携袋入深林,去访那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作者简介:王焕,笔名寻常,2000年生,安徽岳西人。文学热爱者。擅长古体诗词,自编诗集《拾烟集》。岳西县名堂诗社社员,岳西县惜字亭诗社社员,曾获全国第三届百家诗会三等奖、第三届“秦东杯”全国征文比赛二等奖。
来源:向度原创
# 顶端作家造星计划 # #人间# #顶端夜话#
[责任编辑:cqsh]